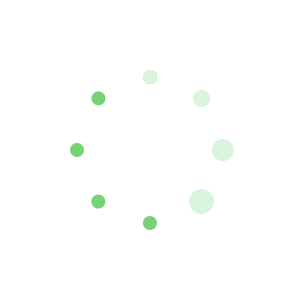晚上,我们住在一对老夫妇开的包早餐的家庭旅店。他们是从英国来的,在澳洲住了25年,男的曾是铁路工程师,女的是博物馆售票员,现在都退休了。于是,把家门打开做旅店招待游客。
我们夜里10点多才赶到这家旅店。两个英国老人西装笔挺地打开门,把我们接进屋,为我们安排好住处后说:“明天早上8点到9点之间,任何时间都可以吃早餐。”然后,很有分寸地同我们寒暄几句,就告辞回阁楼上睡觉去了。
早上一进餐厅,我差点叫出来,那位前铁路工程师居然打着领结在等着我们。我心里想:至于吗,当晚在酒店过夜的客人除我们俩,不就还有一对从墨尔本来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吗?
当我坐下,他用绝对五星级酒店餐厅侍者的标准口气和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问我:“用咖啡,还是茶?”
我盯着那精致的蝴蝶结上面皮肤已松弛但仍挺着的脖子,说:“茶,谢谢。”
当他转过身去,那已盖不住头皮,但仍梳得整整齐齐的银白色头发提醒我:那下面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英格兰头脑。
他从厨房里杷茶壶端来放到我桌上,说:“请慢用。”随手给茶壶盖了个小棉罩。原来是怕茶凉了,给茶壶度身定做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棉袄。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只有一个半手掌大的茶壶罩的面料,竟同桌布、椅垫和窗帘的面料都是一致的。
再仔细打量这个餐厅,有四张桌子,四个同样盖着茶壶的小棉罩,像四只小兔子一样趴在桌子上。墙上挂了六幅淡雅的水彩画,衬托一幅自负的丘吉尔油画。
橱柜上摆着六个英国人家中惯有的高脚银器,使人不由得想起走路都颤颤巍巍,但仍仔细擦着红红嘴唇,穿着丝袜的英国老太太。
我正在神游,那英国老工程师又无声地走到我身边,轻声问:“您要的煮鸡蛋,是要老一点儿,还是嫩一点儿?”
真不愧是英国人!按全世界任何标准,这都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旅店,但它的服务仍是一板一眼,一点不走样的英国程序。
看我们吃完了早餐,他拿来一个精美的笔记本和一盒带针的小旗,说:“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能否给我们签个字并留下地址,再把小旗插到墙上的世界地图中,你们家乡的位置上。”
我问:“这是干什么呢?”
他说:“这代表本旅店曾荣幸地接待过你们,您的家乡可能还会有人再光顾这里,你们插的旗会给您的同胞带来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我和王石对看一眼,分别在还没有人插的香港和深圳的位置上庄严地插上两枚小红旗。看着这些稀稀落落插在世界版图上颜色各异的小旗,我说:“这像太阳永不落的大英帝国。”那老人知道我是从香港来的,礼貌地陪我尴尬地笑了一笑。
插完旗,我问他:“您是怎么来这里的?”
那英国老人竟问我:“我是否可以坐下来同你们谈?”
我大吃—惊,忙说:“这是您的家。”
他说:“但也是旅店。”
王石听了,眉毛往上一挑,说:“这才是职业精神!”
他坐下来一聊,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撒切尔铁政时代的受害者。20世纪7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为提高英国竞争力,除了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外,还关闭了很多政府补贴但没有希望的煤矿。此举引起大规模警民的冲突,铁娘子最后不惜动用军队强行关闭煤矿,那时这位铁路工程师正受雇于运输煤的铁路公司。
他说:“实际上矿工们都知道,煤炭竞争不过石油,煤矿连年亏损,只有靠补贴才能经营下去,总有一天政府补不起会关闭的。但是矿工有选择吗?煤矿越采越贫,他们也没有其他生存技能,关闭矿山就等于判他们死刑,早死当然不如晚死,所以要和政府闹。我那时已有三个孩子,我不想让他们在没有希望的矿区发展。可是人都有惰性,如果不是撒切尔强行关闭矿山,我也不会下决心来澳大利亚的。”
“那为什么是澳洲?为什么是塔斯马尼亚?”我继续问。
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英国人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有一种酸溜溜的情结。我们6000万人挤在又冷又潮又小的岛上,我们生的三个"儿子"却一个比一个大,特别是澳洲才2000万人就拥有这样广阔、阳光明媚的土地。
“可是真要移民到这三个地方,英国人心里都有点怕,不是一般移民的害怕心理,而是怕被"儿子"瞧不起的怕。当人没活路时,就不怕丢面子了。既然从冷的地方出来,就要找阳光最多的地方,于是我们到了这里。
“说起来颇讽刺,我们的四个孩子在澳洲长大后,有三个又移民回英国去了。年轻人要的是热闹和大城市的繁华,所以这么漂亮的岛也留不住他们。”
“那您后悔吗?”我问。
“哈哈!我现在的厨房比我原来在英国的客厅还大;这里的水是全世界最干净的,你们现在喝的就是我从房顶接来的雨水,不用过滤就达到你们喝的瓶装饮用水的标准;这里的纬度度数同纽约差不多,可是冬天平均温度是11摄氏度;还有这里的阳光和空气,都是钱买不到的。人老了,才知道怎么活,我现在真是感谢撒切尔夫人,如果不是她逼我,我可能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