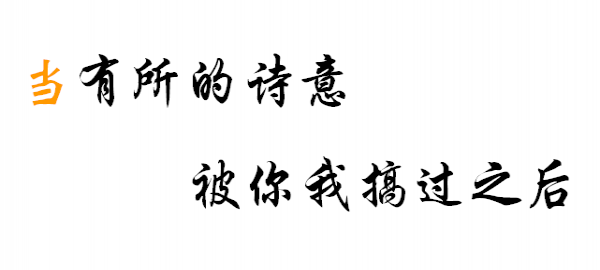
当有所的诗意都被你我搞过之后
作者:顾清平
两年前就听到这张专辑了,往往复复听了数不清多少遍了,狂喜的时候,悲伤的时候,痴笑过,哭泣过,一路听,腰的彩铃般歌声。
是哪一年的夏天,CD还不是像现在这么贵的时候,在台江步行街的那家大音像店,一张张地观察了货架上的CD封面,在货架最底层的一排,《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爸爸他每天起床时候总不得不按下play,狂躁、纠缠、阴暗、晦涩,音乐的歇斯底里,极其稀少的人声,可一旦出现,字字如芒刺在背。两位医院工作者、一个烟厂员工、一位个体户,在国家的西南之境,唱出尖酸刻薄的歌调。
于是几乎是同步的,《他们说忘了摇滚有问题》一上市,我就点下了播放键。
进行曲式的切入,刘涛依旧颓懒得唱腔,我发现被骗了,腰已经忘了摇滚。当刘涛说下“好听得让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当腰细密地铺陈第一首的编曲,当晦喻的歌词布满纸页,他们记起了,摇滚有问题,于是,他们忘了摇滚。
“别人的古迹,别人的公路和床铺,意淫使人疲倦”,鼓点和歌词的循环重复,生息的车水,不竭的奔流,腰是公路中间最慢行的机械,闲情冷眼看着、被周围的事物超越,于是有了“星星挂着的地方,焯起了白色的烟”这样诗性的演唱,有“你总是喜欢这样吗?我只是喜欢你这样。”的缠绵,“所以赶紧老去吧”,十年恶果,悲喜交集。
腰们的玩闹之旅才刚开始,《这宁静的水坑路》,铃声的进入,键盘的往复,怖静的水坑路,我们躺在轱辘下,哭成了泪人。勇气这个东西像是不举的器官,八十年代只是梦境,现实皆虚妄,过往早死寂,你神秘地到达神像之前,我仍要为你,唱首歌。
你忘却了谁?是一个悠久的丑女?来放飞贪污的中老年?还是来收割柔软的青少年?一个唱歌的男人他会告诉你。腰总是不惮于使用最最隐晦的暗喻,既然这个国家已经不允许人们仗言直说了,那何不,把歌唱得再隐秘一些,更隐秘一些。不过是夜班值班室沙发上的蚊蝇,不过是这个国家无知的贱民,站在毫无新意的屋檐下微笑。
腰不是什么密宗的嫡传弟子,只是最市民的狂想:死的时候,身上贴满彩票。所以请施以一点点理解吧,怜悯也可以,反正他们的指指点点都会被质疑为市侩心态,反正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在乎你。直到我们统统晕倒在大国的怀里,是的,在时代之内,我们都是坚韧的爬虫,洗脑之后洗胃,仰起不高兴的圆脸,好可爱。不被允许提及的名字就乖乖地不要再提了吧,即便不引来祸患,也会徒添悲伤 “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才是最大的骗局。这是永远不提,就永远有人不愿提的旧事;这是永远有人不愿提,就永远不提的旧事。1968年4月29日!
谁会在乎呢?更何况是几十年前的事,只是小市民典型的伤感而已,一百三十七人很配合的和很不配合的参与,歌词是美丽的,歌声是麻木,现实是虚伪的。此歌献给1979年所有阵亡者,其中有刘涛的父亲,“谁没有秘密在他心中藏,你在哪里丢弃你忧郁的胳臂?”。
那年的初夏,刘涛看见火车站路口的加油站前,有人踩着三轮车驮半扇猪肉从坡路上飞驰下,面色欣然。他想,他应该是这生活里找对了位置的人。“每条猪,唱同一首歌;在计划里,...